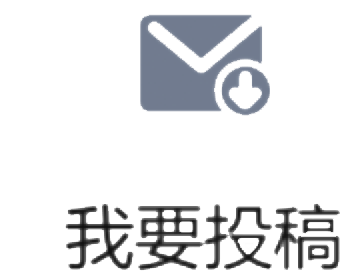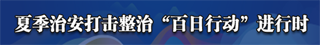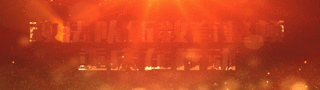|
◎ 丁 懿 年过七旬的父亲,一生不易。 在父亲很小的时候,爷爷就去世了,爷爷的堂兄弟挑着扁担,一头挑着我父亲,一头挑着我姑姑,去见爷爷最后一面。此后一家人,全靠奶奶工资和工厂不多的救济生活,父亲参加工作前,几分钱一碗的重庆小面,他吃不起,也不敢吃——害怕街坊邻居议论:“拿着厂里救济,这家人还有钱在外面大吃大喝。” 受了单位关照的奶奶,只能用更加没日没夜的工作去回馈。无人照看、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父亲和姑姑,有时会从磁器口出发,步行数十公里,到陈家桥大爷爷(爷爷的堂兄弟)家去。这段路途对于孩子太过遥远,走着走着,妹妹再也走不动时,十来岁的少年便背起几岁的妹妹,继续向前走。一路上,憧憬着和善的大爷爷、年纪相仿的兄弟玩伴和一餐温饱。 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,大多没有什么机会正经读书。十几岁初中毕业,也是为了减轻家里负担,父亲早早便顶班进了工厂,成了一名技术工人。曾经问过父亲:“你这辈子会不会后悔没继续读书?不然也有可能成为一名大学生。”父亲认真回答:“没有后悔,家里条件也不允许。唯一有点遗憾,是18岁报名参军没能通过体检。当时面试,招兵的人对我印象极好,要是参了军,也许一辈子就不一样了……” 读书、参军、招工,是那个年代,父亲这样的贫寒子弟,改变命运不多的方式。 然而,没读多少书的父亲,家里却藏了不少书。除了专业的技术书看不懂,小学没毕业的我,便在父亲的藏书里开始读春秋战国故事、隋唐演义、清史演义…… 直到现在,读书依然是父亲的爱好。只是角色调了过来,除了我买的专业书籍,其他的一本不落,他都看。 没读过多少书,似乎也并不妨碍父亲的多才多艺。打篮球,他是厂里篮球队的主力;乒乓球,玩得也很不错;游泳,五十多岁时,还经常横渡嘉陵江。我小学时在家练毛笔字,他教我握笔,一笔一划,横撇竖捺;小时候家里住宿条件有限,他和几个叔叔自己设计,自己动手,没几天便增了个“跃层”出来,至于家里的电器、门窗出点毛病,他琢磨琢磨,总能修。更没想到,上世纪八十年代,父亲便自己买了相机,没事玩玩摄影,绝对的时尚青年! 在曾赫赫有名、父亲为之奉献大半辈子的市级国有企业,突然就走到山穷水尽,不得不破产的境地。领回下岗证,没见他自怨自艾,便想法到处找工作去了。只是人到中年,想要找到合乎技术的工作不易。好不容易找到新工作,但已经与他们那个年代“以师带徒”的工作关系全无瓜葛,一切得从头自学。他并无不适,更是勤勉,但因工资太低,极其俭省。我几次到新单位给父亲送饭,也没觉出什么端倪,直到有一次,母亲淡淡地说:“你父亲在单位上班,工作餐时只吃白饭,从不打菜。”听完,我顿黯然。 从小到大,对于我的学业,都是在学校工作的母亲关心,父亲过问不多。毕业后,他也觉得我工作啥都挺好,只是叫我安心努力,他平淡的口气似乎也并不上心。有次全家外出旅游,网购动车票,显示他的身份证没有通过验证,问他是不是因为以前没有买过火车票,他喃喃地说:“哪里会?你在四川达州工作的时候,我坐火车来给你送东西……”于是记起,刚毕业在外地工作,他带着大包小包坐几小时火车过来,帮我安顿妥当,说明天他还得上班,便又一刻不歇地赶去火车站,买张站票回渝。夏天里他离去时汗水湿透的背影,一下就又上了我的头。 他爱喝酒,但不多。年轻时,每每见此,总不免埋怨。他只是一笑了之。而今,不知不觉我也人到中年,已为人父。奔忙过后,回到家中,饭前总习惯把酒倒上。 他一杯,我一杯。 (作者供职于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,系中国法官文联文学专委会会员) |
 最近更新:
最近更新:
我的父亲

- 石柱县“三个环节”强化规范性文件全流程管理 2024-06-28 20:14:03
- 市司法局调研荣昌区城乡居民精准化普法项目试点及“法治院落”改革试点工作 2024-06-28 20:12:25
- 万盛经开区社区矫正管理局上门为重病社区矫正对象服务 2024-06-28 20:11:11
- 彭水县暴雨突袭 紧急转移530余人 2024-06-28 17:28:39
- 我市6个区县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升为Ⅱ级 2024-06-28 17:25:15
- 万事皆可“刷脸” 处处人脸识别真有必要? 2024-06-14 10:46:54
- 重庆这几招让老百姓真正感到实惠——八条措施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 2024-01-26 10:58:12
- 耕读研学助力高山村落“大治理”——酉阳县涂市镇地灵村“六抓六成”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2023-12-22 10:23:53
- 司法保护让长江母亲靓丽永驻——万州区法院担起“上游责任”,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2023-11-03 11:06:23
- 清廉文化重庆行 | 廉洁清风,从边城吹来…… 2023-09-20 11:02:5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