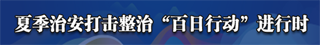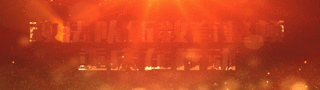|
“普法的关键,就是要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和法治素养。”53岁的张祖筱(张恩铭),祖籍重庆铜梁,现在是南岸区的一位普通市民,2014年起,张恩铭花费十年的精力,编写了《道德教化四字经》和《生活规则三字经》。之后,张恩铭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,将16万字的民法典浓缩为5.1万字的《民法典简洁版四字经》。 “真正意义上的教化,就是把人、事、理全部打通,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方式,让更多的人进入更高的思想境界,具有更高的法治和道德素养……”张恩铭评价自己做的事就是在“渡人”,“普通但意义非凡”。
张祖筱展示自己编写的《民法典简洁版四字经》 十年工夫 编出道德教化四字经 “国无德不兴,人无德不立”。2014年,张恩铭把一直萦绕在心间的念头付诸行动——提炼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编写一部系统性的《道德教化四字经》。 一个会计专业毕业的大专生,为何会萌生这样的想法?张恩铭告诉记者,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,目睹了不少道德“滑坡”和“失范”的现象,遇到不少不讲诚信、不守规矩等情形的困扰,“德滑坡,心切切,兴正道,击奸邪。”张恩铭说自己最担心的便是,“不道德的行为慢慢被人们接受和认可,再不‘刹车’可能会造成道德塌方的局面。” 悠久的文明发展史为中华民族确立了一整套的社会道德标准,它凝聚了东方智慧,埋首故纸,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寻找答案,成为张恩铭的选择。文化程度并不算高的张恩铭,读完了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增广贤文》《少年进德录》《菜根谭》等以德立命、修身治世的古籍著作,开启了自己的明德弘道之旅。 把古代先贤的哲理智慧,用通俗易懂的语言,以四字一句的形式提炼出来,张恩铭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这样的“疯魔”生活中——不打牌也不应酬,闲暇之余苦读苦思,即便是深夜时分,一旦灵感文字涌现,他都会马上记录下来。 “私德不修、公德难立;政德不明,大德不彰。”2024年,张恩铭终于写完了2.9万字的《道德教化四字经》,全文共分34章节,涵盖了天地人道、家庭美德、诚信经商、忠信立世、德被八方、修心悟道等方面的内容。 张恩铭把《道德教化四字经》分享到朋友圈,得到同学、朋友一致好评。受到鼓舞,张恩铭又开始编写《生活规则三字经》,从聚餐、做客、接待,到公共关系、乘坐交通工具、行车、旅游,囊括了市民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行为规范。 在聚餐、做客、接待篇里,他写了这样的提醒:“宴会前,必提醒,开车友,莫喝酒。宴会毕,喝酒嗨,务强调,车莫开。醉酒人,妥护送,法义务,免事故。告家人,说情形,前来接,尽职责。”公共关系篇里又有提醒:“小孩小,管教好,高空物,莫乱抛;浇花草、水淋淋,换位想,楼下邻。讲文明、靠右行,老弱先,顾他人。进电梯、不吸烟、首进人,按开门。”行车篇里他提醒车友:“高速路,变道慎,莫超速,莫龟速。行高速,莫扔物,后果重,命亵渎。错过道,继续行,莫犹豫,莫急停。出事故,车靠边,人撤离,报警及。” “三字经,要牢记,持之恒,习惯成。”张恩铭说,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没有规矩不成方圆,在生活中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,才能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。 简洁风格 又出炉民法典四字经 2020年5月,民法典颁布。“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,道德是最高层次的法律”。张恩铭沿袭了《道德教化四字经》的思路,在理解学习民法典之后,又着手编写张氏风格的《民法典简洁版四字经》。 实际的编写工作并不顺利,张恩铭说,民法典是严谨的法律,需要字句无歧义且表达清晰,有些条款很难用4个字来转述,自己也常常卡壳,只有绞尽脑汁,冥思苦想,斟酌推敲,灵光一现,方可柳暗花明。 “于法无据、不当得利,受损之人,有权请还。”“侵权危及、人身财产,被侵权人、有权请求,停止侵害,排除妨碍。”这些对民法典的概括理解,就出自张恩铭改编的《民法典简洁版四字经》。改编后的四字经朗朗上口、通俗简洁,便于理解记忆和普法宣传。 一直对法律感兴趣的张恩铭,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与法律打交道的经历:儿子在读书时,被同学骗走近万元,张恩铭指导儿子撰写起诉书,自己上诉并打赢了官司;老婆公司因为合同服务纠纷,张恩铭作为代理人与对方聘请的专业律师对簿公堂,凭着仅有的三张微信聊天截图,打赢了看似并无多大胜算的官司。长期的生活历练让张恩铭对合同纠纷和借款纠纷尤其敏感,“很多时候,纠纷往往是因为合同条款有歧义或者证据意识、风险意识缺乏所造成的。”张恩铭说:“这些细腻的东西都无法用四字表达,《民法典简洁版四字经》还需要不断完善。” 尽管不完善,面对凝聚着自己心血的作品,张恩铭还是敝帚自珍,将《道德教化四字经》《生活规则三字经》和《民法典简洁版四字经》都申请了著作版权,并通过朋友圈、视频号、抖音、百度、今日头条等平台尽力传播推广,还计划通过社会讲座、学校演讲、平台宣传、出版发行、印刷成字帖等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作品。 “人的一生只有短短的几十年,还是要做点有意义的事。”张恩铭说:“能够开启民智,觉醒众人,让更多人的法律意识和道德素养得到提高,就是人生最大的意义。” 记者 陈富勇 |
自编简洁四字经 崇德尚法一达人 ——记《道德教化四字经》《民法典简洁版四字经》作者张祖筱

- 用心用情办实事 解决群众“急难愁盼” 2025-04-03 21:19:25
- 加强主体培育、打造活力赛道……万州区这样打造区域最佳营商环境 2025-04-03 18:05:02
- 重庆秀山姑娘李方树被追授为“2024年度深圳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” 2025-04-02 18:59:22
- 提前谋划执法服务举措 全力保障群众平安出行 2025-04-02 17:43:30
- 踏青、祭扫、出游如何安全、畅通?九龙坡警方发布出行指南 2025-04-02 17:41:23
- 酉阳县花田乡何家岩村:党建蓄力激活清廉村居“一池春水” 2024-10-11 11:23:53
- 以法为笔绘就大城善治新“枫”景——万州区钟鼓楼街道全面打造新时代法治建设新地标 2024-08-23 11:05:29
- 万事皆可“刷脸” 处处人脸识别真有必要? 2024-06-14 10:46:54
- 重庆这几招让老百姓真正感到实惠——八条措施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 2024-01-26 10:58:12
- 耕读研学助力高山村落“大治理”——酉阳县涂市镇地灵村“六抓六成”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2023-12-22 10:23:53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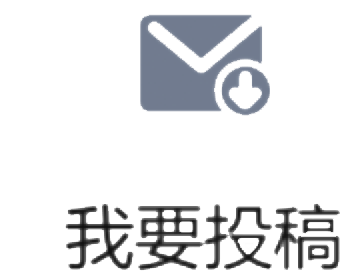
 最近更新:
最近更新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