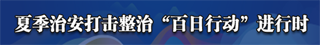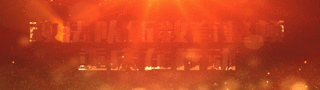|
◎ 罗林衡 毛 票 对毛票,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,那是源于骨子里的爱。 我的家乡金佛山东麓的段家山,曾经是一个极度穷困、缺水少粮的小山村。女儿小时候缠着我教儿歌,我耳边老回荡着母亲常常念叨的那句话:“有女不嫁段家山,太阳出来亲叫唤。”我的童年,就是和着包谷粥、洋芋粑度过的。 父母尝尽了贫穷的苦头,发誓要让我们兄弟俩好好读书,将来能够走出大山。可是他们从土里刨出的粮食,根本供不起我们上学。好在我们家乡盛产煤炭,村里人就像祖辈一样,钻进大地坚硬的内部,从深埋的黄土里取出煤来,卖给四周乡邻烧火煮食。 一入冬,男男女女,老老少少,浩浩荡荡,都涌到我的家乡来背煤,比赶场还热闹。煤的价格嘛,不按斤算,而以背计,大人一背两毛钱,半大孩子一背一毛钱,挣的全是汗水钱。好在背煤的人多,一天也能有个三块、五块的。基本都是毛票,脏兮兮,黑黢黢,几乎辨别不清面额。每晚收工后,母亲有个任务:打几盆清水,把一张张沾满煤灰、汗渍的毛票,放在水里轻轻地漂洗,一张张仔细铺平晾晒。一张张毛票漂浮在水中,父母的眼睛闪着幸福的光芒。 挖煤的工作是艰辛的。父辈们用最原始的方法从事着最危险的工作。一盏昏暗的煤油灯,像腌过了头的鸭蛋黄,昏暗斑驳,对面都不见人。掌子面渗着水,煤壁子泛着幽光。人猫着腰钻进去,煤腥气混着硫磺味直往肺叶子里钻。 好了,不说了,免得又勾起我的眼泪。总之,我就是在一张张毛票的养育下考上了师范,跨出农门,当了教师。直到现在,我都对毛票情有独钟,以至于女儿把我当成了“守财奴”。 炊 烟 晨雾未散,外婆家的炊烟便起了。青灰色的烟柱子摇摇晃晃爬上屋檐,软绵绵地贴着瓦片游走。 我打小跟着外婆生活。一岁多的时候,父母外出,把我交给奶奶照顾,不小心滚进滚滚的煤炉,差点丢了小命。外婆诘责父母的疏忽,把我接到她家照顾。外婆格外疼我,每天早晨,带着铁罐煨饭的清香、混着烧红薯焦香的炊烟,总会把我从梦里拽起来。火灾在我头上留下很大的疤痕,老是有人背后指指点点。更有淘气的小孩,故意扯掉我的帽子来取笑。外婆不管不顾,追着人把他骂住嘴才歇气。一面又低声告诉我,“又不是自己的错,你只管穿自己的鞋,走自己的路”。现在,我做了老师,每接手一个新班级,第一节课能够坦然地给学生讲我头发的故事,都源于外婆的影响。 没有了炊烟,外婆一准出门了。后来才知道,那些年月,邻居们有很多事在等着外婆去做,哪家做的魔芋豆腐不成形,哪家发的霉豆腐长不出白毛,哪家捂的水豆豉拉不起涎丝,都会找外婆去鼓捣一晌。哪家的鸡子中了“土箭”,哪家的奶娃长了马牙,哪家的孩子生疮长脓,也会找外婆去收拾半天。外婆是云南人,随当兵的外公来到重庆,也把那些稀奇古怪的技艺带到了这里。 外婆还有一个拿手的绝活——刮泥鳅症。一天晌午,日头毒得很,炊烟也懒洋洋的。隔壁一个一米八几的精壮汉子,突然肚子痛,大汗淋漓,在地上直打滚。外婆丢下烧火煮饭的苞谷秆,叫人按住汉子,解开他上衣。外婆握紧食指和中指的关节,一边念念有词,一边在用力刮他胸背。等一条泥鳅样的红杠出现,用大拇指卡住泥鳅头,直至红杠消失。晌午饭还没熟,汉子又活蹦乱跳,恢复如初了。 当然,外婆也可能带其他孩子去了。一个生产小组,婴儿出生三天“洗三朝”,宝宝吃第一顿饭“开荤”,多是由外婆操持。外婆喜欢孩子,虽然只有我母亲一个是亲生,另外却有六个抱养的儿女吃她的饭长大。外婆去世时,灵前白花花的一排孝子孝孙哭得死去活来。 世间的外婆都有十二分的善良,和那晃悠悠、怯生生的炊烟一起,构成了让孩子无比留恋的童年。 小青瓦 清晨,慵懒的雨水从山乡的困顿中醒来,鱼鳞似的瓦片,像一尾尾寂静的鱼,湿漉漉的。父亲也是湿漉漉的,赤着上身,打着光脚板,呼哧呼哧地踩瓦泥,头顶笼着一层雾气。 瓦泥是小青瓦的魂魄,得寻最腴润的土。我老家背后几百米,一个叫瓦厂湾的地方,就有上好的瓦泥。黏而不涩,润而不浮,捧一把在手心,能揉出绸缎般的肌理。父亲从几米深的泥坑里掏出瓦泥,又细细挑拣。瓦泥不能掺一颗石子,不然烧出的瓦会漏风漏雨。 踩瓦泥总在暑气最盛的七月,是个费力活。其他人家多用水牛踩,可我家是黄牛,父亲怕踩瓦泥伤牛蹄,总亲力亲为。顶着烈日,父亲跳进泥池,双脚陷进半尺深,汗珠子摔进泥里,炸开一朵朵小花,转眼又被踏平……瓦泥需细细地踩上好几遍,直至漾开一片琥珀色的膏脂才行。 做瓦坯考量的是泥里绣花的功夫。父亲拿着一个水桶样的瓦桶,放在急速旋转的车盘上,然后猛地给它覆上一块整齐的瓦泥。瓦桶飞快旋转,瓦刀蘸水抹平,迅速切下四块上宽下窄的瓦坯。三伏天的工棚像个蒸笼,父亲弓着背重复上千次划泥、收口的动作,后颈晒脱的皮落在泥坯上,成了瓦片里看不见的骨血。 烧窑最为讲究。父亲把干透的瓦坯整整齐齐地码在瓦窑里,封住窑门。然后吧嗒一口烟,郑重地选一个吉时点火。三天三夜,不眠不休,眼睛熬得通红。父亲说烧窑的火候比养孩子更难,火弱了,瓦片是病恹恹的猪肝色;火急了,小青瓦蜷成歪嘴的猪耳朵。 很多年里,一叠一叠,宛如排比句一般的小青瓦,从父亲的手间飞出,在家乡的屋顶一片灿烂。直到水泥钢筋的楼房拔地而起,它才逐渐退出乡村的历史舞台。就像父亲,辛劳一生,佝偻了,苍老了,成了小青瓦般的剪影。 (作者单位:重庆市南川区书院中学) |
毛票·炊烟·小青瓦

- 万盛经开区公证处上门公证 为尿毒症患者肾移植“加速” 2025-03-31 14:35:20
- 万州区开展内河水运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 2025-03-31 14:34:20
- 打造“畅、安、舒、美”出行环境 高速执法部门护航丰都庙会 2025-03-31 14:30:40
- 酉阳县开展“童心相伴”困境和留守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项目培训 2025-03-31 14:29:10
- 巴南区珠江城中学以党旗引领法治护航 谱写新时代育人篇章 2025-03-31 14:22:22
- 酉阳县花田乡何家岩村:党建蓄力激活清廉村居“一池春水” 2024-10-11 11:23:53
- 以法为笔绘就大城善治新“枫”景——万州区钟鼓楼街道全面打造新时代法治建设新地标 2024-08-23 11:05:29
- 万事皆可“刷脸” 处处人脸识别真有必要? 2024-06-14 10:46:54
- 重庆这几招让老百姓真正感到实惠——八条措施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 2024-01-26 10:58:12
- 耕读研学助力高山村落“大治理”——酉阳县涂市镇地灵村“六抓六成”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2023-12-22 10:23:53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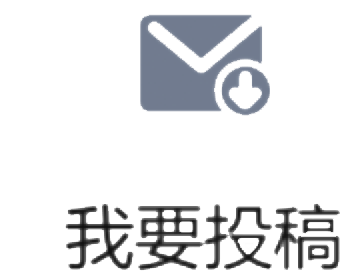
 最近更新:
最近更新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