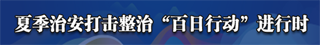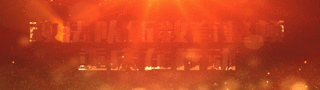|
小面很小,小得可以穿过大针眼;小面很大,大得被人豪气地称呼“铺盖面”。小面很小,小得在街头巷尾的小店门口摆几张小方桌就可以食用;小面很大,大得可以登上大雅之堂。 重庆小面很出名,其中蕴藏着许多重庆人自己的故事……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物资匮乏,生活条件艰苦,乡村生活条件更苦,赶场能吃上一碗小面,那是相当奢侈的事情。 我老家那个乡场,因为两边都是山的缘故,“夹皮沟”的场镇就一条街,从街头走到街尾,零零散散的房子也就排了两百米左右。老街上仅有一家馆子,叫“商堂馆”,员工都是供销社的正式职工。这馆子不大,只有几张桌子,供人们吃包子、馒头、小面。 做小面的炉灶临街,一大早,大锑锅里的水热气腾腾,想要吃面的人先买票,8分钱一碗。做小面的师傅上了年纪,穿着灰扑扑的围腰。他接过票瞟一眼,便熟练地抓起面,往锅里一丢,面条便在沸水中散开,像女人散乱的头发。师傅掌握好火候和时间,用竹子编的漏瓢在水中一旋,散乱的面条规规矩矩进入漏瓢里,抱成一团,然后往早已备好的佐料碗中一放,一碗面就算做成了。食客端着小面,小心翼翼地往桌上一搁,香气扑鼻,慢条斯理地吃起来。 那时小面独树一帜,没有牛肉面、杂酱面之类的高档货。就是小面,吃起也非常享受。面并不多,食客几乎一根一根地慢慢享用,似乎比现在吃山珍海味还舒服。面吃完了,只觉得半饱,没吃过瘾,于是很节俭地把面汤也一并喝下,将8分钱消费得彻彻底底。 老家乡场的“商堂馆”持续了好多年,那个做小面的师傅也一直坚守在那里,就像一棵老树扎根在那片土地。老师傅拿捏面的分量很精准,几乎没有偏差。 “嘿!师傅!……多抽几根面啥。”有食客谦卑地对师傅小声说,恭敬地祈求师傅多放点面时,师傅便会面无表情地说:“我们煮面有规矩,不能一些多一些少,国家的东西哪能随便乱给呢?”说得食客面红耳赤,只好依着老师傅的犟脾气。面没有缺斤少两,佐料也都一个样,大家也觉得公平。 当然,老师傅也有仁慈的时候,偶尔遇到有气无力的乞丐或者吃面需要加点汤的,老师傅也不吝啬。另外用一个碗,用汤瓢舀一碗煮面的汤,滴几滴猪油,放点盐,再放点葱花,葱花四周有点油珠珠,像星宿一样,一闪一闪的,人们把这汤取名叫“星宿汤”。 老师傅对乞丐有些偏心,总是以最快的速度,用漏瓢在锅底转一圈,像耍魔术似的,把碎面条盛在“星宿汤”的下边,让乞讨者能吃点“干货”。乞讨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稀里哗啦狼吞虎咽地吃了面汤,冲老师傅笑笑,算是感谢了。 在外逃荒的人心中很苦,比黄连还苦,苦得难以诉说,这碗看似简单不要钱的面汤,却如行进在沙漠中干渴无比的人,突然得到一瓢水,就有价值连城金不换的感动。“星宿汤”温暖了多少饥肠辘辘的人,在他们眼里,这碗面汤比燕窝汤、鹿茸汤、海参汤都要滋补,成为他们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汤,因为这碗汤增添了活下去的勇气。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,乞讨者获得一份慰藉,老师傅的光明,驱散乞讨者的心理阴影和心中的荒芜。这汤或许救了一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。 煮面的老师傅没有惊人的壮举,但是他的善举后来传为佳话。再后来,人们时常咀嚼这段充满愁苦而又感动的日子,一碗面汤能勾起一份浓浓的乡愁。 这样的日子不堪回首,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几十年的变迁,人们的生活日益富足,鸡鸭鱼肉几乎成了寻常百姓家的“标配”生活。虽然,近些年人们的衣食住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但是小面依然成为人们的牵挂,小面馆在巴渝大地上星罗棋布,小面推陈出新,越做越红火,市民越来越青睐,它成了重庆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 重庆是一个美食城市,小面花样层出不穷,满足各类“吃货”。小面铺天盖地地走进重庆人的生活,让你的味蕾跟着小面的步伐穿行在大街小巷。小面不小,光是名称都能分为好几个类别。从小面的形状而言,有粗刀、细刀;从手工而言,有干面、水面、刀削面、铺盖面;从佐料而言,有清汤面、麻辣面;从辅助食材而言,有牛肉面、鸡蛋面、豌豆面、杂酱面;从面馆取名而言,有“面不改色”“面对面”“当家面”“外婆面”“面面俱到”…… 现在的重庆小面,丰富多彩,味道不一;面馆风格各异,满足食客的个性化需求。更从街边小摊,登上大雅之堂,很多大酒店、大饭店,常在最后上一钵面,供客人享用,且做得精致味美。特别是在老人的寿宴上,一定会有一碗“长寿面”,祝愿老人健康长寿! 重庆小面的故事,在人们的品味中传播,一碗热腾腾的小面上桌,吃的是记忆中的味道,吃的是巴渝大地的小面文化。 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、巴南区作协副主席) |
小面的味道

- 重庆市女性人才研究会与重报集团达成战略合作,共建女性宣传阵地,共促女性人才成长 2025-04-26 15:41:17
- 万州区长坪乡强化重点人群服务管理,督导检查促落实 2025-04-26 13:17:34
- 秀山县人大代表开展专题调研 为农业产业发展“把脉处方” 2025-04-26 12:46:22
- 秀山县要求强化思想政治引领 完善民族区域大统战工作格局 2025-04-26 12:43:51
- 朝天门海事处开展水上搜救演习 强化应急救援能力 2025-04-25 15:14:41
- 酉阳县花田乡何家岩村:党建蓄力激活清廉村居“一池春水” 2024-10-11 11:23:53
- 以法为笔绘就大城善治新“枫”景——万州区钟鼓楼街道全面打造新时代法治建设新地标 2024-08-23 11:05:29
- 万事皆可“刷脸” 处处人脸识别真有必要? 2024-06-14 10:46:54
- 重庆这几招让老百姓真正感到实惠——八条措施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 2024-01-26 10:58:12
- 耕读研学助力高山村落“大治理”——酉阳县涂市镇地灵村“六抓六成”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2023-12-22 10:23:53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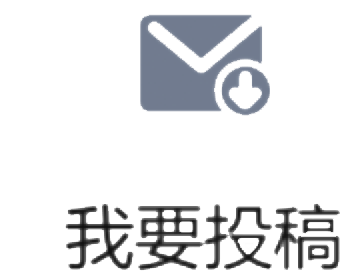
 最近更新:
最近更新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