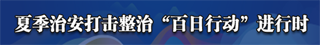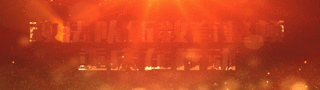|
前一篇诗话已经提到,杜甫《秋兴八首》里的第一首,主要是借巫山巫峡的萧森秋景,以抒发他的难以排遣的“孤舟一系故园心”。王嗣奭《杜臆》精准地指出:“‘故园心’三字为八首之钢。” “故园”的本义,指旧有家园,亦即家乡、故乡。如骆宾王《晚憩田家》诗谓“唯有寒潭菊,独似故园花”,便是用的本义。但“故国”一词,不但可以称旧国、祖国,而且还可以称故乡,如杜甫《上白帝城》诗谓“取醉他乡客,相逢故国人”,便是用的故乡义。而在《秋兴八首》中,本着家国同构的传统文化理念,故园主要是指故国。因此,所谓“故园心”,实质上就是故国之思。 其第二首:“夔府孤城落日斜,每依北斗望京华。听猿实下三声泪,奉使虚随八月槎。画省香炉违伏枕,山楼粉堞隐悲笳。请看石上藤萝月,已映洲前芦荻花。”首联的“京华”即帝都长安,也即是“故园”所在地。长安城地畛北斗星下,又号北斗城。杜甫遥在孤城夔州,望不见长安,只能望北斗,以北斗星作为坐标遥望京华。北斗星固然可以望见,长安城却是绝难望见,因而只能悲伤于心。后六句即由回忆长安岁月,回归到夔州凄楚,寄托其岁月如流,不能再为故国效力的无言嗟叹。 其第四首:“闻道长安似弈棋,百年世事不胜悲。王侯第宅皆新主,文武衣冠异昔时。直北关山金鼓振,征西车马羽书弛。鱼龙寂寞秋江冷,故国平居有所思。”用“闻道”一语引领出前六句,痛陈国家大事的靡乱不堪,桩桩件件无不令人悲痛难抑。自安史之乱以降,盛唐气象已不复存在,代之而起的乃是中唐衰颓,内乱外患兵连祸结,军阀割据,宦官擅权,贵戚勋家却仍然奢靡无度。对于这一切,远窜他乡的杜甫无论怎样痛心疾首,也只能够徒叹奈何。正好比鱼龙寂,秋江冷,杜甫的心境也充满了寂寞和凄凉。回应第二首的“望京华”,第一首的“故园心”,他的故国之思只好落到“平居”,亦即往昔的平日所居上,对盛唐气象追念不已。 后续的四首,便是他“有所思”的具体指向。第五首回忆玄宗主政时期,“西望瑶池降王母,东来紫气满函关”的宫阙之盛,“云移雉尾开宫扇,日绕龙鳞识圣颜”的朝仪之盛,然后追到自己曾“几回青琐点朝班”上。第六首由“瞿塘峡口曲江头,万里风烟接素秋”的“接”字牵引,回忆当年长安城中的曲江一带曾经如何歌舞繁盛。最可把玩的是颔联“花萼夹城通御气,芙蓉小苑入边愁”,以及其尾联“回首可怜歌舞地,秦中自古帝王州”。第七首和第八首,则从长安城扩及周边地区,着力回忆秦中形胜。“昆明池水汉时功,武帝旌旗在眼中”,前一首回忆昆明池景象,那里曾是贵胄显宦游乐之地,暗含着好景不再的意思。后一首回忆渼陂旧游,既以“香稻啄余鹦鹉粒,碧梧栖老凤凰枝”形容物产之美,又以“佳人拾翠春相问,仙侣同舟晚更移”描述士女之乐,然而结意却在自己的“彩笔昔曾干气象,白头吟望苦低吟”。其间的“望”字,与第二首的“望京华”遥相呼应,宣示了终结整体八首诗。 毫无疑问,贯穿始终的故国之思,集中反映出了杜甫的家国情怀和爱国情结。哪管他当时已然年届55岁,多种疾病缠身,漂泊西南已有七年,并且事实上被李唐王朝那个故国抛弃了,他仍然念念不忘那个故国。只不过,与中年时期的长安十年相比,对于传统观念所铸就的忠君与爱国两个向度相交相合,晚年的《秋兴八首》已表现得有所区隔。挑明一点说,已不再一概归于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“葵藿倾太阳,物性固莫夺”,而是更多倾向“乾坤含疮痍,忧虞何时毕”了。 非特如此,这八首《秋兴》还不时对君有所不敬。如第四首的“百年世事不胜悲”,前人已指出“不曰国政,而曰世事者,盖微词也”。如第五首的前六句极状宫阙朝仪之盛,前人也已挑明那是“不言致乱,而乱萌于此,语若赞颂,而刺在言外”。举凡“人主之荒淫,盛衰之倚伏,景物之繁华,人情之逸豫,皆足以召乱”,因而杜甫的“平居思之”并未掩盖微言寓讽,“入边愁”和“回首可怜”无不见讽意。 杜甫对君的这种态度,令人不能不质疑所谓“每饭不忘君”的说法。尽管那个说法始出于苏轼《王定国诗集叙》,但没有定量分析就作出定性结论,也注定属于过分虚夸之辞,不合乎杜甫的生平实际。从长安十年开始,杜甫就不是一个奉行愚忠的人,而是对忠君和爱国有所区隔。流寓夔州后,疑君与讽君的倾向性更强,并且有《诸将五首》《壮游》《昔游》《解闷十二首》等诗表明,他经常性地追昔怀旧指向远不止于君。更何况还如袁枚《随园诗话》所说,“其于友朋、弟妹、夫妻、儿女间,何在不一往情深”,怎么会那么痴呆? |
杜甫的“故园心”

- 大足区金山镇持续开展安全生产百日专项整治行动 2025-04-27 16:42:43
- 荣昌区城市管理局开展“五一”期间城市管理工作培训 2025-04-27 16:19:24
- 荣昌区城市管理局联合区教委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专项督导行动 2025-04-27 16:18:59
- 重庆市女性人才研究会与重报集团达成战略合作,共建女性宣传阵地,共促女性人才成长 2025-04-26 15:41:17
- 万州区长坪乡强化重点人群服务管理,督导检查促落实 2025-04-26 13:17:34
- 酉阳县花田乡何家岩村:党建蓄力激活清廉村居“一池春水” 2024-10-11 11:23:53
- 以法为笔绘就大城善治新“枫”景——万州区钟鼓楼街道全面打造新时代法治建设新地标 2024-08-23 11:05:29
- 万事皆可“刷脸” 处处人脸识别真有必要? 2024-06-14 10:46:54
- 重庆这几招让老百姓真正感到实惠——八条措施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 2024-01-26 10:58:12
- 耕读研学助力高山村落“大治理”——酉阳县涂市镇地灵村“六抓六成”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2023-12-22 10:23:53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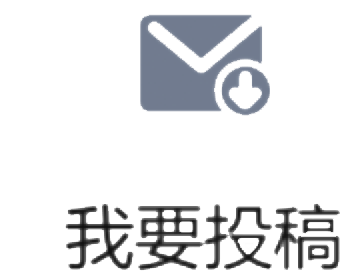
 最近更新:
最近更新: